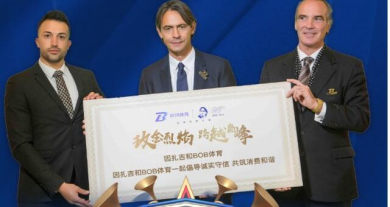汽车16团有个“曾神医”,是一个奇人!
亦兵 亦医 亦像谜
悼忆战友“神医”曾兴祥
文/洪历伟
“人民的好军医曾兴祥”因车祸真菌感染医治无效于2022年11月13日16时15分逝世。曾兴祥生于1954年2月21日,享年68岁。
曾兴祥的逝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切,曾兴祥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噩耗如巨石投入了记忆的深潭般,激起了栩栩如生的小曾年轻之貌,溅出了小曾过于奇特的件件往事,令苍老而为故人伤情的心中涌出了无比的痛惜和遗憾。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十六团的前身成立于抗战胜利前夕,是全军第一支汽车部队。自1950年随十八军筑路进军到2019年军改撤销番号,70年来其浩荡雄风漫卷了整个西藏高原,猎猎军旗下前前后后有数万官兵们驾驶着军车纠纠昂昂而过,车队的后面留下了解放西藏、经营西藏、保卫西藏、建设西藏和巩固国防的壮丽长卷。这是每一届官兵、每一个“十六团人”面对祖国时一生无愧的骄傲。
由于十六团是上级成建制使用的运输力量,所以部队形成的风格和气质是整体感强于个人特色,一代代官兵们也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即大都是一群在平凡、朴素、艰苦、忍耐的前进中去完成使命取得胜利的军人。
而曾兴祥,是这个庞大群体中的一个奇人,一朵奇葩,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战友西去未远,谨悼忆如下,寄我哀思。
小曾是1975年的贵州毕节兵,原三营11连的驾驶员,师傅就是恒。虽同在该营但我认识他较晚,已是在当教导员之后了。
那一年好像全营都在格尔木方向执行任务,11连在前。出发不久就听说前面的11连出了车祸,撞上了某道班正在养护公路作业中的一辆工程车,人车俱伤,但不重。
该道班的上级单位某公路养护段的领导是汉族,不像藏胞那么好说话,非常生气。
我有点着急,就赶到11连宿营的兵站,刚下车就看到11连的指导员凌兴桥喜滋滋乐呵呵地迎了过来。
凌指导员是一个老实人,此刻连队事故在身他却毫无颓意神情轻松让我十分不解。他开口就说“没事没事,曾兴祥一出马就都摆平了”,我这才注意到他身边站着一位个子偏小的战士,他就是曾兴祥。
那时的小曾看上去远较同年的战友年轻,虽然连续半月出发在外依旧衣着整洁。他身材匀称肥瘦正好,一张标准的圆乎乎娃娃脸历经汽车兵生活的风吹日晒依然白里透红,大大的眼睛目光温和,唇红齿白完全没有贵州兵常见的氟斑牙,天生微向上翘的嘴角始终挂着盈盈的笑意,整个人显的生机勃勃,稳定安详。

(迟浩田与曾兴祥亲切握手;左为迟浩田,右为曾兴祥)
我虽然觉得眼前这个眉清目秀的士兵很顺眼,但却不知此次事故为何扯上了他?
凌指导员告诉我这次事故的责任完全在我方。我们的车鬼使神差地就撞上了道班正在作业的同向行驶的工程车。因为撞的太没道理段的领导很生气,一定要全额赔偿。凌很老实又不太善言辞只能不断地陪好话,还诚恳地到这位段长家中去拜望,期以缓和情绪为赔偿谈判创造好一点的气氛。陪他去的正是在11连还算会说话会处事的小曾,开的也是小曾的车。
结果在这位段长家中看到他的妻子躺在床上,一问才知已病多年,行动困难需人照顾。小曾立刻主动向前问诊、安慰并施以按摩,还取出随身携带的什么针给她扎针治疗,没想到立刻得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让这位久苦于妻子病痛的段长看的呆了,立刻转怒为谢连称“神医”。小曾并不多言。只说大姐明天还需再扎几针,再给配点药,一定很快就能好的。段长大喜过忘请求凌指导员让小曾留下来两三天。
凌见事态逆转就说了些军民一家鱼水情深但因小曾自驾一车,部队的运输任务不能耽误等等,反倒把这位领导急得不行再三恳求。于是凌导员慷慨地答应留下小曾,由自己来代开小曾的车,完成任务返回时再来接他。凌指导员这番话赢得了段长的千恩万谢。
几天后车队返回时段长夫人已有大好,而且该段的工人们听说天降“神医”在此也纷纷前来求诊。小曾来者不拒,就在段长的办公室里几乎给所有人都看了病,而且似乎都是手到病除,赢得了连片的惊叹和感激。
此时的11连与养护段的关系已完全不像是车辆事故的对立两方而是亲如家人一般,哪里有人再提事故和赔偿之事?
我听后大为称奇,就问你怎么懂医?他只是说他的师傅是一位苗医老人,入伍前跟他学的。我说万一你给他们治坏了怎么办,岂不是更难处理事故了?他只是淡淡地一笑回答我说,“教导员,那是不可能的”,让我对他顿生信任。
凌指导员此时又对我说,这种事情已发生过几次了,每次只要有曾兴祥在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故。我大喜说小曾是个宝啊,以后我们三营无论哪个连出了事你都要把他借给我去灭火,专门处理三营的事故。凌自豪地说“好!”
小曾的名气自那时鹊起渐渐名声在外,不断有人来团寻医。但在十六团他仍然是一名普通的驾驶员,仍然整天挂着笑意,谦恭和平。
忘了小曾是什么时候提的干,但不是在我们三营当排长而是调到了团卫生队当医助。听政法说是杨启纯政委某次带他去处理事故时见小曾为藏族小孩用手法接上了胳膊断骨,认为他是个人才就把他提了起来并放在团卫生队。
可卫生队虽然是部队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对医疗技术的要求并不算高,懂点针灸之法,也会每年自采药材自制黄连素片等中成药,但仍然是以西医为主的,他们完全看不懂也不能接受小曾这种民间的江湖医术,更不敢让卫生队为他的治疗负责,而官兵们则少有人去找他看病,大家更熟悉更信任更习惯的还是卫生队的医生和他们的打针吃药挂点滴,这使小曾很难在卫生队拥有自己的一个诊位。
但是小曾并不为自己的这种处境感到有丝毫的尴尬和为难,因为他的医术本身就不属于这个传统的军队医圈,他也不喜欢军队的组织纪律给予他的有限自由,在脱离了汽车和运输任务的限制后,他毫不犹豫地展翅偏离十六团的建制,他的心、眼、医都完全朝向了团大门以外,朝向了那些质朴淳厚并仍然贫困的藏胞们,他认为(事实也证明)那里才是他的医疗舞台和人生天地。
不为本团战友们和汉族人群所相信的曾医生在给藏族同胞们看病时却效果灵验,很快便巩固和扩大了关于“曾神医”的传说。
小曾就和卫生队这样两不相干地存在着,名气越来越大,病人的层次也越来越高,竟然还成了阿沛.阿旺静美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副主席和自治区巴桑,丹增等高层领导人的常客,连军区首长也常常直接从团里将他接走给自己按摩等,他和这些高层首长的个人关系也好到近到远超我们的想象。
或许是看他年轻质朴乖巧,或许是他的医术真的了得 ,首长们都非常地喜欢他也非常地爱护和关照他,这保护了小曾在团里的自由度。

此时的小曾实际已经脱离了十六团的这块天地,只是占着十六团的一个编制、一个职位而已,他已成为一个自由,自主,既行于地又高来高去的人。
但是他依然友善谦恭地微笑着,依然尊敬礼貌地对待过去的每一位首长和战友,依然热心踏实勤谨地对待和帮助他人。他大方地出借自己的日本相机,殷勤地用自己的另一架“宝丽来”一次性成像机为大家拍照,虽然时尚超前,却无论在何时何处何事上都始终努力地保持和维系着自己与十六团之间关系的亲密性与舒适度,对此我有亲身体会。
我当主任时痛感政治处因写稿写材料多,办公用纸量远大于司、后,但在拉萨印制政治处专用信笺的价格太高增大了办公成本,一日突然想何不平日打草稿时就用白纸,在修改定稿后再用公用笺誊写上报,便可缩小部分开支?于是找来曾兴祥请他回家问问在军区印刷厂工作的夫人能否帮忙。
小曾一口应下说马上让老婆安排。第二天黄昏时分我俩便派了一辆大车前去,此时厂里已经下班厂区里空空荡荡一片寂静。
刚到车间门前,只见一个高挑苗条扎着工作劳保围腰的年轻女子已候在此。她指挥驾驶员停车,指挥小曾和身旁的一位年轻的男性工友上车卸纸,再运到和码在机器上,口令简洁指挥准确行云流水般地就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其干练麻利熟练的程度令人叹服。
她就是小曾的夫人,一个相当漂亮热情,有眼色有礼貌的能干女人,配小曾绰绰有余,难怪恒称其为“小凤仙”,在厂里和团里都小有名气。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工厂里的手工裁纸。裁刀高过半人弯如新月,背薄锋利,刃口也如新月般发出寒光。
在“小凤仙”的检查指挥下那位小伙子手按刀柄谨慎沉稳地起刀,下刀,抽刀,裁刀一遍遍的如月升月降般地诗意起伏,一令令白纸便在悄然无息中变成了8开、16开、32开等我们需要的规格,整洁地停在了工作台上。
只是至今30多年过去了,一想起当时裁刀的那道锋芒,犹觉得脖子上会发凉。
“小凤仙”的热情与小曾比是外向外露的。她用车间的材料替我们分装好后,我问他她需要多少加工费,她开心地一笑说我们是用自己下班后的休息时间偷偷地给你干的,车间头头们根本都不知道还要什么钱?我非常感谢她但她的口才让我连感谢话几乎都说不出来。
她指使小曾把这些纸包一一装上车后我们就准备走了,但是她却突然对已坐在驾驶室里的小曾说“曾兴祥,你坐上面去,不要在这挤到主任了!”小曾立刻麻溜地爬上了车厢。我对她说天都黑了又起风,就坐在驾驶室里吧,她却把车门一关对我说,“主任你不管,他一个年轻人冷点怕啥子嘛!”小曾也坚决不下来。我知道她这一切都是在帮曾兴祥,心里不由得叹道真是一个长得漂亮,做事漂亮,为人处世也漂亮的女人啊!
但恒后来告诉我他们没有走到头,让我深为惋惜。
为了医患双方的方便,小曾选中了团南北公路西侧三营出口处一间破旧不堪的大房子,这是营房股用以堆放旧营房拆迁后堪用的旧门窗等的库房,本身也是危房但位置醒目,与机关和各营区均有一段距离不会形成干扰,于是每天这间房子的外面就有很多的藏胞排着队等待“曾神医”就诊。他们安静有序的队列和风尘仆仆灰头土脸的形象在十六团的营院里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我和恒当了团里的主官后自然更不会为难他,但从政工的角度讲我总还是有些不放心,其中最担心的就是他会不会出个医疗事故而把十六团牵连进去?所以一天专门抽时间耐心地在他的“诊所”也就是那间老房子里去观看他的“神医之技”。
我进去后对他说,小曾,这么冷你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呢?他说你看看这里哪里还有空处?果然一大半是堆积到天花板的旧物,剩下的地方迎门摆着一把破旧的三抽桌和和一把破旧的椅子,这就是他的“诊断室”。他的身后也是堆积到快到天花板的干枯的、半干枯的、还算新鲜的各种草枝树枝状的植物,他说都是各种草药。
在这个四处透风逼仄的空间里,没有白大褂,没有听诊器,没有助手,没有药房,也少见寻常中医“望闻问切”的“神医”曾兴祥用半汉半藏的语言无比耐心和颜悦色地给这些人看着病,暖如春风,其对底层藏胞亲近和诚恳的态度让我深愧不如。
他给的药就是在各堆植物上或多或少地抓上一些,还有一种自己研磨的粉末则分别用一分、两分、五分钱的硬币舀出来(这种控制药量办法让我目瞪口呆),“药袋”就是废报纸,整个环境和过程随意简陋的让我不敢相信,更谈不上卫生和消毒。
更让我既吃惊又开眼界的是他给病人扎针。他用的针完全不是我所见过的针灸医生使用的那种纤细精巧的银针,而是一根大过过去老人们绗绵被所用的那种大号缝衣针,黑黢黢的“丑针”。他把这根黑黢黢的针往一个装着同样黑黢黢散发着酒气液体的普通瓶子里沾了一下,点火,于是整个针体便冒出了带着酒味药味的火苗。及火苗盛时针亦热时就着火苗就把这根大针扎进了病人的某个穴位,一阵“滋滋”作响入之甚深,逐渐熄灭。这种从未闻之见之的独特针疗术让我心惊肉跳而病人却并无大的不适表情,实在奇哉。
他的行医实在超出了我的认知,待看完病人后我便把疑虑之处逐一问他。例如为什么不把脉?他说我们是苗医,也可不用把脉。又问你这些药怎么都像枯草一样难看?他说你们常说“草药草药”,这就是草药,不像中药需经泡制,为苗医用药之长。再问为何给药时不用戥子计量?答曰“抓药抓药”嘛,用戥子就不叫“抓药”了,用手就行,我的手准得很。还问了这么多药材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有自己採的,有买的,更多的是这些藏胞们送来的。至于扎针他解释道他这种叫“火针”,因为兼具针扎、药入、热敷的作用,效果好于中医的银针,是师傅独传于他的绝技。等等。
至此我才明白,虽然可能因为常年缺医少药致使藏胞的疗效好于汉人,但小曾也绝非是浪得虚名。
仍然忧心未断的我说,你这一套未经过科学和医疗部门论证认可,治出问题来怎么办?他还是当年的那句话,“那是不可能的”。我说我们十六团不是医院,万一治疗中出了问题,藏汉关系军民关系的这个责任团里负不起,你可不可以不要给他们看了呢,至少不要在团里看病?他说不是我要他们来,是他们来找我的。你都看到了每天这么多人又都是穷人,很多还是拉萨以外牧区来的,我怎么拒绝?我又能怎么办?我又不收他们的钱,药都是自己动手自己掏腰包给他们配的,我能到哪里去?
我一想也是,还真没有看到有人给他付费的,只是走时不停地弯腰合拾不断感谢,所以无言以对。从此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不了了之了。
进入九十年代后,不知何时他悄无声息地调离了十六团,走前也没有给我打一声招呼,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也没问过,心中反而松了一口气。
1993年春末夏下初,我突然被调入军区干部部,由一个边防军区后勤部队的普通政委变成了领率机关要害部门分管任免工作的领导。为了适应这种巨大的变化,更因为当时的干部任免事项十分繁重,我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不是在办公室里熬夜就是下部队考核干部,忙的昏天黑地心无它顾,直到几个月后张震副主席到西南战区视察时接见军区机关全体干部时,我才发现曾兴祥也在队列中,原来他早已在我之前调到了军区政治部办公室,任秘书。虽然很惊异很开心但实在是太忙了,还是没有时间接触叙旧。
再到又是几个月后他来到我家,我才知道他竟然和我住在同一栋宿舍楼里,只不过因各在两头的不同单元难以碰面,所以我和妻都非常高兴。
这一次的见面小曾又再次让我吃惊。
他拿出了一叠照片给我看,竟然都是和江泽民主席的合影,而且还有些是仅他和主席两人的合影。印象最深的一张是江主席以大家都熟悉的姿势双手抚肚舒坦地坐在一张长沙发里,小曾站在他沙发的靠背后面双臂伸开撑在上面,身体前倾目光向前表情顽皮,像一只展翅的大鸟飞翔或护守在主席的头上,而江主席则笑容灿烂。
原来是江主席任军委主席后第一次下部队就视察成都军区,在这里历时一个多月的行程里,小曾是伴随的保健工作人员之一,主要工作是做按摩。看照片上这份亲热的程度,江主席对小曾的服务一定是很满意的。
妻很吃惊,说你还会按摩呀?他仍是过去那种浅浅的一笑,说“扶姐,这很简单。你要不要试一下?”正好这段时间妻肩痛不已自然是要的,于是小曾就在我家的一把椅子上给她做按摩。也未见有什么特别的手法特别地用力但妻直呼“好痛”,小曾不为所动毫不理睬,继续施以重手法按摩,不多一会儿就结束了。此时妻惊喜地发现按摩后的止痛效果出奇的好,肩也出奇的舒服(所以这次听说小曾走了还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了这一段往事),说按的时候很痛,但按过之后感到整个人都好了,实在是太舒服了。不过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奇特和有效的按摩了。
我目睹这一切心中默念“神乎其技”时,小曾又拿出一个普通的光秃秃酒瓶,里面装的又是黑乎乎的液体。他说这是他专门用心为我调制的药酒,好的很,让我一定只能留给自己喝不要送人。我说我不太信这些,他正色道,他的酒保健作用很强,能壮阳,现在在东南亚都有影响,当地很多华侨大老板和他联系,说给他投资,让他以自己的名字办个公司生产,运到东南亚后保证畅销赚大钱。
后来按他所说我在北较场的菜市场洛阳路的中段果然见到在一段底层和二楼之间的外墙上赫然挂着“四川兴祥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几个足有半米的大字,但我没上去看。
这次见面我俩都非常地开心,高原的往事更是让我们情感交融温暖温馨甚慰离愁,只是当天我还要加班未能尽兴。
原以为来日方长见面不难,没想到不久之后我又调到十三军炮旅了,离开了政治部。后来再到了遵义,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噩耗至时已别有近30年了,不禁怅然而悲。
往事在前感慨万端,曾兴祥在十六团里只是一名普通的干部,在藏胞心中则是一名尊敬的“神医”, 在高层领导身边时又是一名优秀的保健员,而到了一些商家眼里或许就是一棵“摇钱树”了。但对我而言,他是战友,是好人,是十六团滋养出来的奇葩,更是我心中一个又一个的谜。
他既服务于国家的最高领袖又行善于西藏的贫困民众,既扎根于自己的团队又活跃于高层机关和首长间,所有的作为和轨迹既公开又隐秘,既合乎情又违于规,是一个既平常无华又光芒眩耀的人,尤其看到到讣告上的子女竟有五、六人之多时,不觉生出“谁人尽知曾兴祥”的叹息。
但是不管怎么说,曾兴祥没有给我们十六团丢脸,是一个热心重情的好战友和对藏胞亲爱友善的好医生,我非常地怀念他,希望他一路走好。
兴祥,你的战友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亲爱的战友曾兴祥安息吧!
2022年11月15日至19日夜

作者简介:
洪历伟: 十八军后代。曾任西藏军区某汽车团政委、成都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兼任免处长、某旅政委、某军分区政委等职,现军休干部。
延伸 · 阅读
- 2022-08-22持梦启程 共创未来 创维
- 2022-05-01南宁青秀山五一期间举办
- 2022-03-19猎鹰搏击俱乐部~珠宝玉
- 2022-02-26淄博有个满满正能量微信
- 2022-01-30北京凯旋之旅汽车租赁有
- 2021-10-01奇瑞汽车领导一行来访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