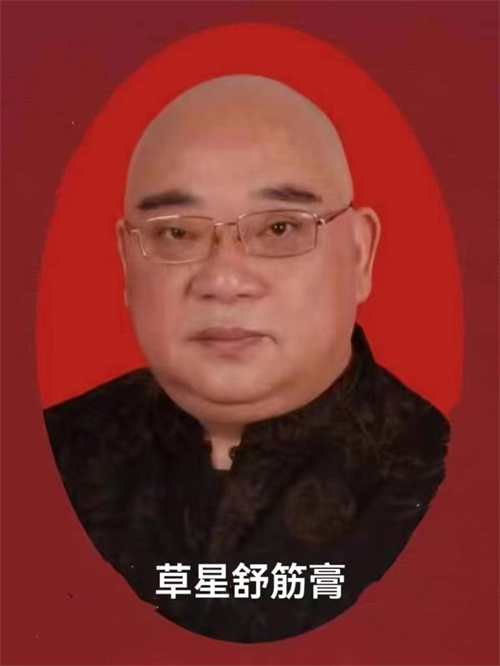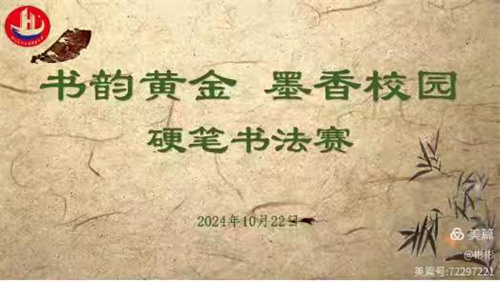【听泉轩微言】第1509期
2025-08-05 10:03
徐立泉
织梦技术论坛
踩士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老家湘阴县城里,没有公交车交车,除了零星的公务车外,只见自行车和踩士的河流蜿蜒流淌。我们这些年轻职员,每日奔波于公务之间,常遇路途遥远或天气恶劣。那时,一种叫“躁士”的人力车,便是我们的代步工具。车夫们几乎是一个模式三轮车+一顶草帽+一条毛巾+一个盛茶的可乐瓶。看到他们就有一种心酸的感觉。
起初,坐与不坐,像心里纠缠的线团。我总在犹豫:身为干部,让百姓拉车,岂不是役使劳力?可若拒绝,又怕冷了车夫们眼巴巴盼着生计的眼神,更兼风雨寒暑难耐。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坐。不忍心看着他们那种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客人而又离开的失望的眼神。然而,我给自己立下规矩:遇有上坡,必下车同行,搭手助力;只走大道,不劳车夫拐进僻远小径;付钱时,不多给一分,这也是一种尊重。亦不少付一文。记得一个冬夜,朔风割面,我坐老冯同学的踩士回家。行至长坡中段,我便下车,双手抵住车架。老冯口中呼出团团白雾,花白头发在车把前微微颤动。我们一齐用劲,车轮一寸寸碾上坡顶。汗水悄悄渗入我的衣领,却仿佛也把冰冷的隔阂一同融化开去。车杠末端磨得发亮的手把,在夜风中显得更加晶亮,像是为这无言的协作在眨巴的眼睛。
多年后回望,那些朴实的“踩士”早已消隐于时代的尘烟。但老冯们俯身踩车的身影,在我记忆的底片中反而越走越清晰——他们以汗珠兑换生活,脊梁负起生计的重量,竟比坐车的我更显出一种昂然的高度。
原来劳动尊严的碑石,无需颂词堆砌:它就在脚踏车上坡时掌心的温度里,在每一次俯身用力、每一次对他人劳力的体恤与自重之中,悄然矗立。(徐立泉)
起初,坐与不坐,像心里纠缠的线团。我总在犹豫:身为干部,让百姓拉车,岂不是役使劳力?可若拒绝,又怕冷了车夫们眼巴巴盼着生计的眼神,更兼风雨寒暑难耐。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坐。不忍心看着他们那种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客人而又离开的失望的眼神。然而,我给自己立下规矩:遇有上坡,必下车同行,搭手助力;只走大道,不劳车夫拐进僻远小径;付钱时,不多给一分,这也是一种尊重。亦不少付一文。记得一个冬夜,朔风割面,我坐老冯同学的踩士回家。行至长坡中段,我便下车,双手抵住车架。老冯口中呼出团团白雾,花白头发在车把前微微颤动。我们一齐用劲,车轮一寸寸碾上坡顶。汗水悄悄渗入我的衣领,却仿佛也把冰冷的隔阂一同融化开去。车杠末端磨得发亮的手把,在夜风中显得更加晶亮,像是为这无言的协作在眨巴的眼睛。
多年后回望,那些朴实的“踩士”早已消隐于时代的尘烟。但老冯们俯身踩车的身影,在我记忆的底片中反而越走越清晰——他们以汗珠兑换生活,脊梁负起生计的重量,竟比坐车的我更显出一种昂然的高度。
原来劳动尊严的碑石,无需颂词堆砌:它就在脚踏车上坡时掌心的温度里,在每一次俯身用力、每一次对他人劳力的体恤与自重之中,悄然矗立。(徐立泉)
收藏
举报
延伸 · 阅读
- 2025-07-20中国皇室艺术作品展在日
- 2025-07-01【热烈祝贺】世界传统文
- 2025-06-10【礼赞七·一】中医精深
- 2025-05-16【以中药之史,鉴文化之
- 2025-05-09探访处州历史奥秘 寻觅
- 2025-05-09【探访处州历史奥秘 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