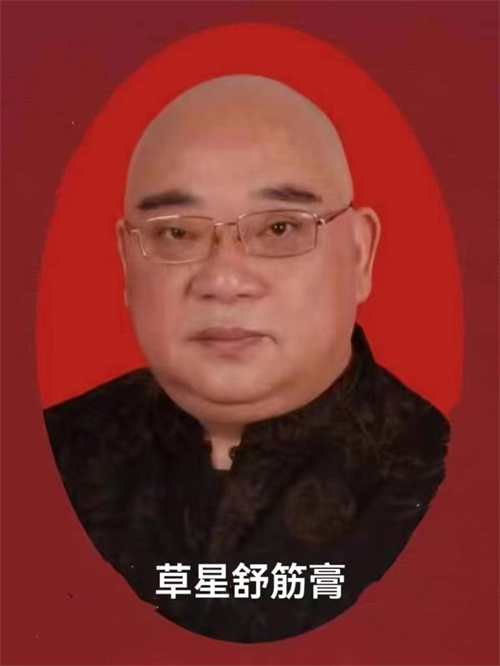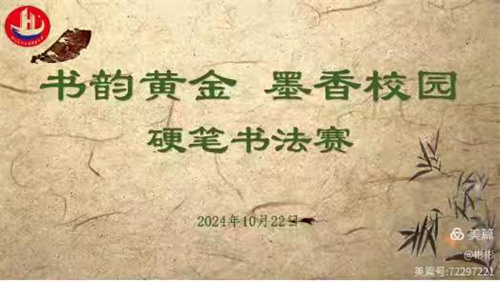那一盆“清水”与觉醒的光芒 ——记《清水洗尘》联考讲评课
2025-11-15 17:14
胡姣艳
未知
当全省联考的试卷翻到迟子建《清水洗尘》这一页,课堂的焦点,聚集在了那个执拗的少年——天灶身上。
“同学们,读完文章,你们觉得天灶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抛出第一个问题。学生们若有所思,却很难找到一个精准的词语来概括他。
我换了一种问法:“那么,你们是否支持天灶,支持他非要用一盆干干净净的清水洗澡这个决定?”
“支持!”这一次,回答异口同声,她们脸上漾开喜悦的笑容,仿佛是代入了天灶的处境,为他争取到的公平而感到由衷的胜利。
“可是,为什么支持呢?”我笑着追问。
教室里的笑声更大了,她们互相看着,眼神明亮,却给不出一个准确的表述——那种感觉就在嘴边,却找不到合适词语的状态,正是思维火花即将被点燃的前奏。
“好,那我们换个思路。”我适时地将话题引向她们最熟悉的生活,“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年时,我们都会收到红包,这笔叫‘压岁钱’的钱,虽然是给到你的,但支配权好像从来不在你手里。爸爸妈妈总会说:‘我先帮你保管着。’”
话音未落,教室里“嗯嗯”的附和声已经响成一片,所有人的眼神都在空气中寻找着共鸣。
“然后呢?”我继续引导,“这笔钱,后来可能变成了你的学费、书本费,或者,就这么悄悄地‘消失’了。直到某一天,你心里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等等,那是我的钱啊!它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决定怎么使用它?’”
我停顿了一下,环视着她们,清晰而郑重地说道:“如果你曾有过这样的念头,同学们,那么恭喜你,你的成长历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到来了——这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
“哇……老师,这个词好高级啊!”一片惊叹声在教室里荡漾开来。这惊呼,并非因为术语本身,而是她们终于为那份深藏于心的直觉,找到了一个确切的名字。
“它其实并不抽象,”我告诉她们,“这种对‘什么属于我’‘我感受如何’‘我的价值在哪里’的觉察与追问,我们并非第一次遇见。”
“比如,‘女性意识的觉醒’。” 我将目光投向学生们稚嫩的脸庞,“晚明汤显祖的《牡丹亭》上演时,曾发生过一个非常动人的现象。大家想象一下:当时许多养在深闺的女性,她们坐在台下,看着台上的杜丽娘为了一个梦中之情,可以缠绵而死,又可以执着而复生。她的生命完全被自己的情感所驱动,这份炽热和勇敢,像一道强光,瞬间照进了许多观剧女性的心里。”
我放慢语速,试图引导她们共情:“那一刻,她们可能会下意识地去对比自己的人生,并且思考:难道我这一生,就只能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安排,做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吗?我内心那些真实的情感、那些未曾言说的志向,它们就不重要吗?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我的价值,难道仅仅在于扮演好别人期望的角色吗?”
“杜丽娘用她超越生死的行动,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却像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无数女性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涟漪。她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命运,这种朦胧的、对个人情感价值与生命自主权的珍视与探寻,便是女性自我意识在历史长河中一次动人的觉醒。”
学生们目光炯炯,仿佛也跟随着我的描述,回到了那个戏台之下,感受着那份跨越时空的内心震撼。
“那么,文人的自我意识,又是如何觉醒的呢?” 我将话锋一转,抛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并试图引导她们进行对比思考。“在谈到这个之前,让我们先回想一下——我们课本里学过许多先秦诸子百家的文章,谁能说说,他们都写了些什么?核心思想是什么?”
课堂瞬间活跃起来。
“《寡人之于国也》!”一个女生抢先回答。
“对,孟子在那篇文章里,是在跟谁说话?核心是在谈论什么?”我追问。
“在跟梁惠王说话……是教他怎么治理国家,让百姓安居乐业。”
“非常棒!”我肯定道,“还有吗?《劝学》?”
“荀子在告诉我们学习的意义和方法!”另一个声音响起。
“没错,而《劝学》的最终目的,也是培养能治理国家的‘君子’。”我补充道,“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墨子奔走呼号,他们著书立说的核心听众是谁?最终目的又是什么?”
“是各国的君主!”学生们逐渐理清了思路。
“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让天下变得更好!”
“总结得太好了!”我接过她们的话,“所以,在先秦时期,那些最杰出的文人思想家,他们的学问与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政治的,是向君主提供治国方略,我们称之为‘代圣人立言’。他们的‘自我’,是融入到一个更大的、服务天下的集体理想中的。”
“而历史发展到魏晋,情况发生了巨变!”我的语气也随之扬起,“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他们的画风彻底变了。他们不再那么热衷于围着政治打转,而是高呼要‘越名教而任自然’。”
讲到嵇康,我用了更富有情感的语气:“最经典的,就是嵇康临刑前。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从容不迫,只要求一架琴。在刑场之上,万众瞩目之下,他弹奏了最后一曲《广陵散》。曲终,他慨叹的是个人的绝艺即将失传,而非政治遗言。这个姿态,潇洒、悲壮,他用生命最后的时间,捍卫的不是政治理想,而是一个独立个体的精神尊严和艺术追求!他在用行动宣告:我首先是我自己,然后才是别的任何角色。 从先秦的‘为天下立言’到魏晋的‘为自我存在’,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转变。”
从身边“我的压岁钱去哪了”的懵懂追问,到天灶对“一盆清水”的执着坚守;从杜丽娘故事引发的女性内心波澜,到文人们从“代圣人立言”到“为自我发声”的精神转向——一条关于“自我”如何被发现、被珍视、被捍卫的精神线索,清晰地浮现出来。
课程接近尾声,我望着她们明亮的眼睛,做了深情的结语:“哲学家叔本华有一个深刻的观点,他认为,人认识到‘世界是我的表象’,是一切哲学思考的起点。这听起来很深奥,但其实,它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它就藏在你对自己压岁钱去向的那一丝疑惑里,藏在天灶对那盆清水近乎固执的坚持里,也藏在那些观剧女性的沉默泪水和嵇康的绝响琴音里。当一个人开始将目光从外部世界收回到自身,审视‘我’的感受、‘我’的权利、‘我’的价值时,一个更真实、更辽阔的精神世界,便由此开启了。”
这堂课,始于一份试卷上的一篇小说,最终却通向了我们每一个人。那盆名为“天灶”的清水,洗去的是一年的尘垢与委屈,照见的,却是那个正在苏醒的、独一无二的——“自己”。
“同学们,读完文章,你们觉得天灶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抛出第一个问题。学生们若有所思,却很难找到一个精准的词语来概括他。
我换了一种问法:“那么,你们是否支持天灶,支持他非要用一盆干干净净的清水洗澡这个决定?”
“支持!”这一次,回答异口同声,她们脸上漾开喜悦的笑容,仿佛是代入了天灶的处境,为他争取到的公平而感到由衷的胜利。
“可是,为什么支持呢?”我笑着追问。
教室里的笑声更大了,她们互相看着,眼神明亮,却给不出一个准确的表述——那种感觉就在嘴边,却找不到合适词语的状态,正是思维火花即将被点燃的前奏。
“好,那我们换个思路。”我适时地将话题引向她们最熟悉的生活,“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年时,我们都会收到红包,这笔叫‘压岁钱’的钱,虽然是给到你的,但支配权好像从来不在你手里。爸爸妈妈总会说:‘我先帮你保管着。’”
话音未落,教室里“嗯嗯”的附和声已经响成一片,所有人的眼神都在空气中寻找着共鸣。
“然后呢?”我继续引导,“这笔钱,后来可能变成了你的学费、书本费,或者,就这么悄悄地‘消失’了。直到某一天,你心里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等等,那是我的钱啊!它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决定怎么使用它?’”
我停顿了一下,环视着她们,清晰而郑重地说道:“如果你曾有过这样的念头,同学们,那么恭喜你,你的成长历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到来了——这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
“哇……老师,这个词好高级啊!”一片惊叹声在教室里荡漾开来。这惊呼,并非因为术语本身,而是她们终于为那份深藏于心的直觉,找到了一个确切的名字。
“它其实并不抽象,”我告诉她们,“这种对‘什么属于我’‘我感受如何’‘我的价值在哪里’的觉察与追问,我们并非第一次遇见。”
“比如,‘女性意识的觉醒’。” 我将目光投向学生们稚嫩的脸庞,“晚明汤显祖的《牡丹亭》上演时,曾发生过一个非常动人的现象。大家想象一下:当时许多养在深闺的女性,她们坐在台下,看着台上的杜丽娘为了一个梦中之情,可以缠绵而死,又可以执着而复生。她的生命完全被自己的情感所驱动,这份炽热和勇敢,像一道强光,瞬间照进了许多观剧女性的心里。”
我放慢语速,试图引导她们共情:“那一刻,她们可能会下意识地去对比自己的人生,并且思考:难道我这一生,就只能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安排,做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吗?我内心那些真实的情感、那些未曾言说的志向,它们就不重要吗?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我的价值,难道仅仅在于扮演好别人期望的角色吗?”
“杜丽娘用她超越生死的行动,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却像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无数女性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涟漪。她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命运,这种朦胧的、对个人情感价值与生命自主权的珍视与探寻,便是女性自我意识在历史长河中一次动人的觉醒。”
学生们目光炯炯,仿佛也跟随着我的描述,回到了那个戏台之下,感受着那份跨越时空的内心震撼。
“那么,文人的自我意识,又是如何觉醒的呢?” 我将话锋一转,抛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并试图引导她们进行对比思考。“在谈到这个之前,让我们先回想一下——我们课本里学过许多先秦诸子百家的文章,谁能说说,他们都写了些什么?核心思想是什么?”
课堂瞬间活跃起来。
“《寡人之于国也》!”一个女生抢先回答。
“对,孟子在那篇文章里,是在跟谁说话?核心是在谈论什么?”我追问。
“在跟梁惠王说话……是教他怎么治理国家,让百姓安居乐业。”
“非常棒!”我肯定道,“还有吗?《劝学》?”
“荀子在告诉我们学习的意义和方法!”另一个声音响起。
“没错,而《劝学》的最终目的,也是培养能治理国家的‘君子’。”我补充道,“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墨子奔走呼号,他们著书立说的核心听众是谁?最终目的又是什么?”
“是各国的君主!”学生们逐渐理清了思路。
“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让天下变得更好!”
“总结得太好了!”我接过她们的话,“所以,在先秦时期,那些最杰出的文人思想家,他们的学问与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政治的,是向君主提供治国方略,我们称之为‘代圣人立言’。他们的‘自我’,是融入到一个更大的、服务天下的集体理想中的。”
“而历史发展到魏晋,情况发生了巨变!”我的语气也随之扬起,“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他们的画风彻底变了。他们不再那么热衷于围着政治打转,而是高呼要‘越名教而任自然’。”
讲到嵇康,我用了更富有情感的语气:“最经典的,就是嵇康临刑前。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从容不迫,只要求一架琴。在刑场之上,万众瞩目之下,他弹奏了最后一曲《广陵散》。曲终,他慨叹的是个人的绝艺即将失传,而非政治遗言。这个姿态,潇洒、悲壮,他用生命最后的时间,捍卫的不是政治理想,而是一个独立个体的精神尊严和艺术追求!他在用行动宣告:我首先是我自己,然后才是别的任何角色。 从先秦的‘为天下立言’到魏晋的‘为自我存在’,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转变。”
从身边“我的压岁钱去哪了”的懵懂追问,到天灶对“一盆清水”的执着坚守;从杜丽娘故事引发的女性内心波澜,到文人们从“代圣人立言”到“为自我发声”的精神转向——一条关于“自我”如何被发现、被珍视、被捍卫的精神线索,清晰地浮现出来。
课程接近尾声,我望着她们明亮的眼睛,做了深情的结语:“哲学家叔本华有一个深刻的观点,他认为,人认识到‘世界是我的表象’,是一切哲学思考的起点。这听起来很深奥,但其实,它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它就藏在你对自己压岁钱去向的那一丝疑惑里,藏在天灶对那盆清水近乎固执的坚持里,也藏在那些观剧女性的沉默泪水和嵇康的绝响琴音里。当一个人开始将目光从外部世界收回到自身,审视‘我’的感受、‘我’的权利、‘我’的价值时,一个更真实、更辽阔的精神世界,便由此开启了。”
这堂课,始于一份试卷上的一篇小说,最终却通向了我们每一个人。那盆名为“天灶”的清水,洗去的是一年的尘垢与委屈,照见的,却是那个正在苏醒的、独一无二的——“自己”。
(作者:临湘市职业中专 胡姣艳)
收藏
举报
延伸 · 阅读
- 2025-11-14BJ40增程元境智行版限时
- 2025-11-13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 2025-11-13青春心向党 奋斗十五五
- 2025-11-11“文化力量:传承与奋进
- 2025-11-10笔墨绘天河 精神永传续
- 2025-11-08广州从化冬种开耕,5万